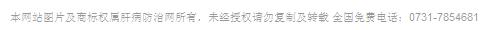张莉:先锋文学缺少代表作年轻人更爱看《平凡的世界》
编者案:1985年前后的85新潮,文学界出现了马原、格非、孙甘露等人的先锋小说,陈东东、王寅、欧阳江河等人的先锋诗歌群体,音乐界出现了瞿小松、陈其刚、谭盾等人的先锋音乐,电影界则有陈凯歌、滕文骥、何平等人的探索电影。
几近每隔数周,一种新的风潮、新的宣言便会发表。风潮迭起的年代,先锋文学应运而生,3十年过去,它长成了甚么样子?它如何影响了后来的年轻人?11月27日,以通向世界性与现代性之路为主题的记念先锋文学3十年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昨天,澎湃新闻()刊发了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在论坛上的发言。下文是文学评论家、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在论坛上的发言。
天津师范大学张莉
我将新一代作家作品作为检视先锋文学影响的镜子。从这面镜子里,可以看到先锋文学当年的文学观、文学趣味如何被扭曲,如何被继承。换言之,如果我们把先锋文学视作文学之钟,那末,从年轻一代作家那里,我们可以听到它的回响,自然,也可以看到它的困窘。
回响之一是,先锋文学建构了八十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青年读者的文学趣味,尤其是7零一代作家的文学趣味乃至语感。先锋文学3十年,正是7零一代作家从孩童成长为中年,由文学少年成长为新一代作家的3十年。如果有兴趣去读七零一代作家的读书随笔和小说讲稿会发现,他们浏览和爱好的作家作品百分之八十与先锋作家们喜欢的作家作品相同或相近,而另百分之210,则非常有可能是当年那代先锋作家。一个作家的少年期和青年期的文学趣味如何建立?无外乎是浏览和模仿。一方面喜欢他们所喜欢的,一方面渴望写出他们那样的作品,先锋文学对7零一代作家的影响是渗透式的,年轻一代的成长得益于对文学偶像的学习。正是在这样的学习进程中,一代作家的文学趣味逐步构成。
这是新的、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价值观完全悬殊的文学观。尤其是新一代对纯文学这1概念的认领。纯文学与先锋派紧密相干,它看重语言,叙述方式,讲求语法和句法,致力于语言的探索,致力于摆脱政治话语而回到文学本身。7零以后出身的作家们对纯文学是全盘接受并深入内心。这是硬币光泽的一面,而另一面的反应则是年轻作家不由觉地划走,他们笔下历史背景的逐步模糊,他们沉迷日常生活,看重个人生活和个人成长而不愿去触及社会题材。换言之,先锋文学以后,有关宏大的、社会的、政治的思考成为新一代作家所刻意躲蔽的。
如果说纯文学观念是先锋文学在7零作家一代那里的重要回响,那末另一个回响则是关于写甚么和怎样写的认识。新一代作家通常在访问中会刻意强调他们看重怎样写。虽然在写作手法上也未见有何重大突破,但这1认识却深植于心。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固然,写甚么在他们那里则变得没那末重要。与此同时,他们中很少有人认为作家是知识分子,更很少有作家认为文学写作也是一种社会行动。
不过,7零一代作家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对写作的理解也非原封不动。
大约2010年前后,又一批新的七零后作家出现,比如阿乙和曹寇。在媒体的讨论和介绍中,他们被认为是先锋的、深具先锋文学精神的新一代,虽然这类评价不乏出版推行的因素,但得到读者和公共媒体的广泛认同也值得关注。为何其它七零后作家其实不被认为是先锋的,而只有他们被贴上这样的标签?
重要的是他们面对现实的态度。在现实眼前,这两位作家与以往七零后作家的不同在于,他们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不认同、不屈服、不让步。他们并不是一笔1划去描摩现实。在他们的笔下,现实与文本出现了某种奇特的关系,文本为现实提供了某种镜像,它是现实的一种反应,但这类反应并不是直接的。他们关注当下生活,也有非虚构作品。
在当代中国,非虚构突然出现缘于写作者强烈回到现场的写作欲望,但那种流行的非虚构与阿乙、曹寇的非虚构有明显差异:前者明显寻求一种对现实的参与,其中有强烈某种济世情怀;后者的写作则是,不济世,不启蒙,他们寻求的是极简、深入、零度写作,重视事物逻辑,出现出来的文本则有一种荒谬感。
阿乙和曹寇对文学的理解使我想到余华当年在《虚伪的作品》中所说: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致使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觅新的表达方式。寻觅的结果使我不再忠实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情势。这类情势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但是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固然,让人想到先锋2字的也不仅仅是以上两位,在弋舟、廖一梅、李浩等人的作品里,也能感受到他们与八十年代及先锋文学之间的亲缘关系。或许年轻一代作家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认自己受益于先锋文学,但是,读者却常常从他们的文本中感受到先锋派在某一瞬间的复活。
与现实的对抗与紧张关系、疏离感是先锋文本的重要特点,如何理解虚构与真实/现实的关系是先锋文学遗留下来的至为宝贵的文学财富,也是一代作家在情势探索外壳之下所做出的最核心文学贡献。余华、格非、苏童在年轻时期完成了向惯例和写作成规的挑战,从而也为自己开出了一条新路。
但是,今天的新一代作家只是偶有几位意想到如何理解文学与现实这1问题的重要,大部分作家面对现实的态度是和缓的、亲密无间且不带反思意味的,这也意味着先锋文学的重要财富并未在更多年轻人那里得到回响,年轻一代也谈不上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创新之路,这是记念先锋文学时我深感遗憾的。
以上谈的是先锋文学的回响。但这样的回响也与先锋文学的困窘相伴。这类困窘首先在于,脱离历史语境后,它注定要被不断地误解和误读。
比如,前文提到的纯文学这1概念。今天,纯文学在新一代年轻人那里被认为是阔别政治的,是去政治化的。但是,在最初,先锋文学的纯文学概念并非如此,它有它的面向,有它的所指,正如吴亮先生所说,先锋文学的出现有它的时间和空间。
而且,当年的他们在文本中提到个人,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个人也有重大差别。当年,纯文学的说法既有文学层面的寻求,也有本身的思想内涵,它乃至影响了当年人们对个人与社会白癜风正规医院责任的重新认知。换言之,当年先锋文学的去政治化姿态也是政治行动的一部分。今天,如果我们只将先锋文学理解为纯洁的文学情势的探索,那是我们理解问题的偏颇而不是事实本身。
不过,此刻,在这样的场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讲授者,我要坦率指出先锋文学浏览史上一个使人不快的事实。当我在课堂上不遗余力地讲述先锋文学时发现,90后一代虽然愿意了解这1文学事件,但在浏览当年的先锋文本时表现出极大的不宁愿。
先锋文本与当下学子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膜。相对而言,他们更乐意去浏览《平凡的世界》,由于那里的生活和情感更容易让人产生亲近与认同。这是先锋文学在文学浏览史上遇到的为难。
我们固然不能一厢情愿地把这1困窘全部推到年轻人浏览趣味的守旧,先锋作品在更年轻一代读者那里被冷落的事实明显也说明:先锋派作品其实不完善,这些作品走出文学史课本很有可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所以,今天的我们看到,先锋文学只是作为一种潮流一种观念被认识,我们只能对作家们如数家珍。
那末,我想说的是,站在三十年后返观,在先锋文学正盛的三四年间,先锋文学提供的是一种文学观和写作观,而可能并未产生经典代表作。恐怕那批先锋作家都已意想到这一点,因此,如何使先锋的情势不流于空转,如何将一种先锋的情势与所表现的现实生活进行完善结合是困扰先锋作家至今的写作困难。
三十年来,余华、格非、苏童一直在努力克服这1困难。我想,正是他们延续不断地自我探索和自我完善,才有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河岸》《黄雀记》,《江南三部曲》。他们在八十年代以后以更加完善的白癜风能彻底治好吗作品与更广大读者产生了共鸣,这些作品不需要依赖历史语境、不需教科书的解读便可独立存在。正是这些优秀作品的出现使今天的我们和未来的文学史需要不断地回想先锋文学之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使今天和未来的读者不能忘记和疏忽这三位优秀作家其来有自。
今年夏天,我曾在《先锋派得奖了,新一代作家应当突起》1文中提到,衡量一代作家的贡献不在因而否获奖,而在于他们是不是推动过中国文学的发展。今天,不管看到了怎样的困窘,我都坚持认为,先锋派文学对中国文学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新一代的作家和批评家,我和我们以后的许多青年人都是这个推动的受益者。
首先出现的是叙述语言,然后引出思惟方式。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援用过李陀所说。这段话我一直印象深入。我以为,如果没有先锋文学的极端的情势探索和语言实验,就没有先锋一代作家的成长。但这句话今天想来也可能有沦为美丽修辞的危险三十年后,我们新一代的具有变革意义的思惟方式真的被那种叙述语言引出了吗?站在今天返观,我是不安的,由于我的答案远不乐观。
转载请注明:http://www.cbusw.com/zlff/5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