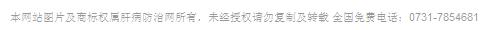。在中国,耕种田地被认为是一种迫于无奈、毫无希望的生计。农村凋敝,农民辛劳而几无所得,这让他们成为城镇化浪潮和一个又一个打工致富故事里遥远而模糊的注脚。但我们在寿光发现,农民的形象清晰了起来,中国原来有这样一群职业农民的存在。大棚庇护了寿光的菜农,让他们得以逃离大多数中国农民背井离乡的命运。他们在土地上生活,亲近农作物,像了解自己的体温一样了解它们的温度。他们通过劳作赚得收入与尊严,享受到完整家庭的温暖和乐。靠着自己的双手,故事里的孙会祥成为一个尊严、自信的农民。直到洪水冲毁了他的美好生活。大棚寿光有二十多万个蔬菜大棚。卫星图片上,白色矩阵把田地均匀地分成一格一格。在这片没有任何丘陵的广阔平原上,它们简直到处都是。被毁的大棚已经无人打理,在风中萧条。重建大棚日子未知,农民再次农作可能要等到明年了。这种在农田上用水泥柱、竹竿、铁丝、土墙搭建起来的塑料大棚,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他们在这里播撒种籽,挥洒力气与汗水,最终,给他们生活的奔头。8月19日,大棚遇到了最强劲的敌人。“温比亚”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上游水库的泄洪带来的洪水,让二十多万个大棚几乎全军覆没。洪水过去十五天了,这些大棚还在田野里蔫头蔫脑地趴着,刚铺上的鸡粪肥被污水浸泡后散发出刺鼻的臭味。现在正是栽种季,但嫩苗被洪水泡过,好像烧焦了一般,枯黄地立在田地里。一个菜农带着幸存的3只大白鹅视察了自家大棚坍塌的棚顶,走下来的时候什么也没说。一种无望而迷茫的情绪开始蔓延,在寿光,我遇到的所有农民都表达了出奇一致的观点:宁愿塌的是家,也不愿意塌大棚。种大棚还能把家再建起来。大棚塌了,啥都没了。大棚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踏实感:在这个世界,有所劳就有所得。大棚里暖烘烘、湿哄哄的,这是一个人造的温室,热量进来了出不去,湿气蒸腾起来,作物可以快速地生长。7月堆上肥料,8月栽下种苗,只要你勤劳又灵敏,你会看到枝条一天天拔节,叶片一天天肥大,果实慢慢挂满枝头,结上一茬又一茬。在二十多万个大棚中,菜农孙会祥的长米、宽20米、高7.8米的棚是纪台镇青龙孙村最大的一个棚。3个月前,他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把自家4个大棚推倒,整修成一个新式大棚。新式大棚能够储存更多的热量,蔬菜产量能上去。从年开始种大棚,他一直是村里最愿意学习新技术的菜农。这意味着一大笔投资。他去银行贷了十万块钱,又东拼西凑借了一些,还从农资店赊了账。他和妻子李凤忙活了足足三个月,建起了一个超级大棚。“有那么长的没那么宽,有那么宽的没那么长”,夫妻俩喜欢得不得了。一整个夏天,两人被晒得皮肤黝黑,腿上被蚊虫咬得疤痕累累。但他“怀着美好的愿望”,新大棚能在两三年内把成本赚回来,还能给家里赚上更多的钱。正在住院的孙会祥作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要把市里的房子卖掉,用于还清大棚负债和房贷,这次灾难让孙家“一夜回到解放前”。这个42岁的男人是村子里最勤快的那种人。即使是去年冬天急性阑尾炎发作,疼得要命,医院保守治疗了几天,那时候正是第一茬辣椒下来的时节,他放不下地里的活儿。现在,这份勤劳使他付出惨痛的代价。超级大棚被连日的大雨灌满了水,然后,决绝地倒塌了。从东侧一根水泥柱的断裂开始,当着孙会祥的面,咔嚓咔嚓倒了一片。又累又急,孙会祥的阑尾炎又犯了,急性转成了慢性,还能忍,他就着甲硝唑片,开始抽水。在田间地头,菜农们都秉着一种除了这个无事可做的心态,在自家的大棚抽水作业。排完水之后能怎么办,他们也不知道。但地上还是铺满了密密麻麻的排水管道,有的村子因为排水的问题打了起来。孙会祥买的两个水泵交替工作,但还是无济于事,大棚的水抽走一部分,又再泛上来。洪水第七天,医院。这下有时间了,他终于做了阑尾切除手术。躺在病床上,他开始不断回味这个苦涩的现实:二十多万,打了水漂。孙会祥在病床上奄奄地躺着,对任何事情都提不大起兴趣。发洪水那几天,四处漫溢的水流带来了上游的活鱼,有人跑去抓鱼,但孙会祥早没了那份心情。他和妻子时不时看看
转载请注明:http://www.cbusw.com/kxyy/142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