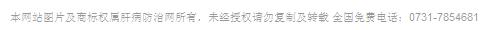5月25日上海解放。8月1日爸爸当机立断带着我们全家北上了,这足见他当时对解放寄予的希望和热情。因为他想到了解放后恢复教育会急需各种教材,并带来出版业的兴旺。到北平后不久,他自告奋勇按照地下党预先安排好的路线,先到香港,然后乘船到山东石岛,接着护送叶圣陶夫妇等一批民主人士。在穿越解放军防线时,他假称“被俘”,辗转来到北平,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我们是8月4日到北平的,记得火车抵达前门车站已是夜里,我们乘坐一辆墨绿色的四轮马车来到台山会馆。台山会馆在西四西安门外的丁字街,路北,大门西侧是一家“居士林”。大约是年冬天的一个凌晨,一个油条摊失火把西安门烧掉了。那时我已在香山慈幼院读小学。
香山慈幼院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应留有浓重的一笔。第一任院长是中国第一总理院长熊希龄,一代名医施今墨曾任副院长,李大钊、胡适、顾兆麟、张伯苓、雷洁琼、康克清、谢冰心等一批社会知名人士都曾出任过学校的董事会董事。
香山慈幼院原来确实在香山,当时占用的是香山别墅和昭庙等废旧的建筑。解放军打进北京时,党中央设在了香山,毛泽东、江青住进了双清的别墅。出于安全的考虑,慈幼院就迁到了城里府右街北头的西安门大街26号。年国务院参事室又占用了这个校址,它又迁到了阜成门外的白堆子,一度曾变成外语学校,现在更名为“北京市立新学校”——一个类似劳改单位的名称。香山慈幼院的命运之所以每下愈况,就是因为在它的全称上有“私立”二字。香山慈幼院的没落消失是中国政治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教育的耻辱,是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悲哀。
私立香山慈幼院是一个慈善机构,解放前收养了一批社会上无人抚养的孤儿,从婴儿到小学六年级都有。每个班的学生大大小小,年龄参差不齐,他们叫“正生”。我们是自费入学的,相当于现在的“择校生”,称为“副生”。学校管理非常严格,门禁尤严,平时学生不准走出校门,周末出校门必须到教导处领取一块白色的一指宽的“校牌”,交给门卫。学生犯了错误,就要罚掉校牌,剥夺每周出外的唯一一次机会。学校里还留有一些其它的惩罚的手段,如罚站、用戒尺打手心等,这也许与当年大量流浪儿童入学有关。
我和元锴入校的时候,慈幼院已经迁到了城里。当时爸爸妈妈在开明书店的天津分店工作,于是我们送进了这所寄宿学校。大约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独立的生活。那段经历对我们的一生都非常有益,特别是当我们的家庭面临绝境的时候,我们表现出了异常的忍耐力和适应力。爸爸妈妈非常强调对我们进行“独立为生”的教育,对我们的发展给予了相当大的空间。看似很放纵,但实际上却让我们在挫折和教训中得到了锻炼。
学校原址是一个日本特务机构,学校的马路对面是北平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大教堂,离教堂不远则是臭名昭著的草岚子监狱。校内所有建筑都是日式的,楼房一排一排的,每排很长,极像是日本兵营。一排楼是教室楼,有三层,一楼外有三根四方的黑色大理石石柱,我们常以其做掩护,玩一种相互追逐的叫“不许动”的军事游戏。楼下有阴森的地下通道,我们常撬开盖板钻进去捉迷藏。
二排楼是宿舍,也是三层,想来是当年的日军营房。屋顶是铁皮盖的,冬天西北风一起,发出剧烈的撕裂般的声响,十分恐怖。每一间宿舍里摆着二三十张双层床,可屋里只有一只取暖的铁炉,冬天很冷,我们要下很大决心才敢钻进冰凉的被窝,早上醒来时,被子边沿常挂有一层白霜。屋子中央放着一个尿桶,早晨由值日的同学抬出去。二排楼的北侧挂着一口钟,学校的一个姓包的工友负责敲钟报作息,他光头瘦长,敲钟时,一手叉腰,一手拉绳,一下一下敲为起床,连敲两声为上课,连敲三声为开饭。
三排楼是食堂,只有一层。当年学校的伙食很差,基本上是三顿粗粮,我们经常吃窝窝头,有玉米面的,还有糜子面的。解放后靠战争时期留下的一些美国救济品的剩余物资维持,印象最深的食品就是土豆粉罐头,味道与现在麦当劳的薯条相近,但它做得很短很细,是土豆磨成粉压合而成的工业品,放在热水里可调成糊糊喝,也可以当零食吃。每当老包敲钟的时候,学生们就唱“当当当,当当当,窝头咸菜小米汤”进入饭堂。每顿饭前大家围坐在饭桌旁,由教导主任训话。训完话,他大喊一声“开动!”于是大家就拿起筷子疯抢,几分钟时光就风卷残云般地将饭食一扫而空。
年,我8岁直接进入了四年级插班。其实我的二、三年级因为战乱就没得上好,再加上到了北京听不懂普通话,而且住在学校不习惯,老是想家,功课一塌糊涂。学年结束,全班52人,我列45名,成绩单的备注栏写道:“经教导会议议决,须经新生入学考试及格方得升级”。爸爸决心让我留级一年,重修四年级。第二年果然有了进步,一下升至18名,除“写字”外,其它主课都考在90分以上。
年,我家搬到了东四灯市口附近的演乐胡同,那是开明书店的宿舍大院,共有三进,住了十几家人,大多是从上海开明迁书店来的。不久,外公也从上海过来,暂住在这里。那个院落的东面隔墙就是商务印书馆,我们常进去玩。四姨家住在后院,我们两家合灶吃饭,过得十分融洽。合用的保姆姓白,我们叫她白大娘,她是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中年妇女。
到了五年级,我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这一变化源于两件事:一是我急发阑尾炎,住进医院,之前不久,医院开阑尾炎,给我动手术的是同一位女医生。这是医院。近年身体健康检查,外科大夫问我:“做过手术吗?”我撩起上衣让他看刀痕,他问我:“什么时候?”我说:“60年前”,他笑了。自从动了那次手术,我好像一下长大了许多,当年的操行评语突然出现了“聪明”二字。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个叫张东生的,家住门头沟,父亲是铁匠。这个同学比我大三四岁,每天督促我学习,查我的作业和笔记,一起复习功课。和我一起被督管的还有一个与我同龄的学友,叫刘纪圣。他是个公子哥儿,他的父亲从新疆起义过来,家庭条件不错,也很不用功。张东生长相很凶,对我们管得很严,经常向我们瞪眼动手,我们三人结成一组,终于到六年级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考上了中学,我考上了当年已经十分难以录取的北京八中。自从上了中学,这两位同学再没有见到过,但这段友谊却一直未被忘记。
还有一事让我记忆终身,那是一次罢吃学潮。当年的伙食又差又不卫生,常能吃出老鼠屎。一天几个年龄大的正生闹了起来,用筷子敲碗敲桌子,大声喊话,后来发展成全饭堂的吵闹。教导主任闻讯赶来,当场叫出三个十五六岁的大孩子。可能是因为当时我说话声音比较大的缘故,他也怒气冲冲地指着我,让我跟上一起去办公室。我生性胆小,不知会有什么惩罚等着我,怯生生地尾随其后。当走到二排楼的拐角时,教导主任刚刚拐过身去,走在最后的一位大同学突然转过身来对我轻声说:“跟着我们干什么,滚!”一脚踢开了我。这一事情后来的结果怎样我不清楚,那位大同学叫什么名字也始终没有打听,但这一场景,我一直记忆到今天。年“6·4”之后,我充当了当年那个大孩子的角色,在北体大保护了几个年轻学生和老师。我常想,这时隔37年的两件事是否在冥冥中存在着什么因缘?这后一个故事容我在以后的故事里慢慢道来。
考中学前,爸爸已经从开明书店出来,追随叶圣陶公公先到了华北联合出版社。这个出版社设在西单菜市场隔壁的白庙胡同里,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前身。我爸爸从此成为公职人员,开始吃“供给制”,即什么东西都以小米的数量折实。后来人民教育出版社搬到了佟麟阁路乙10号,我家也从东城搬到了西城。同时,香山慈幼院也再次搬到郊区。
我的童年始于动荡,即将在一场更大的动荡前结束了。
白癜风医院成都哪家好白癜风治疗最好方法转载请注明:http://www.cbusw.com/zdff/53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