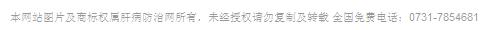在医疗效果描述上,有一句流传甚广,我们耳熟能详的话叫: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ToCureSometimes,ToRelieveOften,ToComfortAlways
这被刻在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碑上,讲述了为医的三种境界,这也是众多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这句话是特鲁多医生向更早的一位医学大师,现代外科学之父,安布列斯·帕雷(AmbroisePare)致敬的一句话。
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很多器官移植,植皮甚至是变性手术,都已经屡见不鲜了。可是在几百年前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人类在对外科伤口上的处理,没有多少的一些办法和手段。像之前,人得了阑尾炎都无法处理,急性穿孔那时死亡率在90%以上;得了急性胆囊炎,可能会导致胆汁性腹膜炎也是致命的。甚至一个痔疮也是有极高的风险。像大唐王朝首辅,宰相张居正,就是《万历十五年》里面那个一条鞭法的改革家,他就是得了痔疮,那个时候手术处理不了。痔疮是直肠和肛门之间一处类似静脉曲张的这样一种病。所以只能用在那个地方去敷药,去缓解他的症状,然后一点点的药物中毒,也提早的离开了这个世间。
为什么外科手术的效果会这么差,然后会有这样的问题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情况。第一就是疼痛。第二是不容易止血,导致失血过多。第三,是细菌的感染引起的各种并发症。
讲疼痛,有一个段子叫“一人手术三人死亡”。就是之前的手术师的技艺的比拼,在于他动手术的时间速度的快慢。因为太疼了,时间长了病人受不了,所以一般的情况,几个大汉压住那个伤者做截肢,然后这个大夫他的速度就特别快,有时候一刀下去,病人的腿也截断了,压住他大汉的手也截断了,旁边有个人觉得鲜血横飞,太血腥了,吓死过去了。然后被切断手的那个人,过了几天感染也去世了。一场手术三个人死了,死亡率高达%。
就算是熬过了疼痛,有的时候止血也处理不了,因为你的组织表面处理一下,他不能够很好的止血,因为它里面有动脉管,他才是这个失血最主要的一些环节。就像春秋战国时期,成语卧薪尝胆的主人公越王勾践,他的对家,吴王夫差的爸爸叫阖闾,是一代君王,当然那个时候秦始皇还没有推行帝制,但也算是南方吴国的部落联盟首领,一国之君。然后他就在打仗的过程中被敌人砍掉了脚趾,然后几天以后就去世了。有人讲是砍掉脚趾引发了急性的心梗,也有人讲是因为当时没有处理的手段,包扎的手段导致过度的失血休克去世了,所以你看是多么的危险。
不仅东方,西方也是一样。像古希腊的神话人物,阿克琉斯。阿克琉斯是大英雄,半人半神,盖世的英豪,武功过人,在特洛伊战争中被射中脚后跟,然后就死了。这就是著名的阿克琉斯之踵。你们想他那么一个大英雄,怎么射中脚后跟都没办法处理呢,其实很多后人猜测就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并发症导致的。当然我们要美化英雄,说这是他的命门,当年没有浸泡在神的药水里等等。所以,其实东西方都差不多。
正是因为这些外科手术的效果很差,处理的手法又野蛮,像活人的屠宰现场,所以外科手术师的这个地位也比较低,就不被人重视。那个时候其实医疗体系内部是分几个层级的,最高层级是一些知识精英阶层把持的经验哲学,他们讲人体的一些理论,推行古罗马盖伦的体液学说,就跟我们东方讲阴阳五行差不多。中间阶层是一些汤药,或者敷一些膏药,以及做一些伤口包扎的这些医师。最底阶层才是动大刀子,截肢,放血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个时候的这个风险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了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兰西,就跟我们这边的康熙大帝是同一时期,路易十四得了一个叫肛瘘的疾病,他在全国找技术最精湛的手术师来给他动这个手术,找到一个外科医生。医生说,陛下,你要给我6个月的时间,我要在76个类似的病人身上先做练习,才敢给你进行这个服务。可见其实这个医生自己对手术也没有太大的把握。那个时候很多的人得了结石不得不做手术,因为得了结石的人很疼,这种疼,有人描述就是比生孩子难产还要疼。所以,虽然手术死亡率很高,但是人受不了,还是要求助外科医生。那个时候的段子就是要想做这个手术,还得配一匹快马,就当那个病患的家属找你麻烦之前,你可以跑到下一个村子,找到另一个被病魔折磨得不行只能向你求助的病人继续你的手术之路。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的外科手术师,其实和另一种职业是捆绑在一起的,就是理发匠。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理发店门口有一个红蓝白的一个灯,很多人误以为是法兰西的国旗,其实不然。其实红色代表了动脉血,蓝色代表了静脉血,白色是绷带,就那个时候的理发店它还做一些外科手术的业务,把这个灯挂在外面,就提醒病人,我们这边不仅可以理发,也可以给你整个牙齿,切个痦子,或者放血等等做一些这样的业务。因为那个时候盖伦的体液学说非常盛行,啥啥病都放血了。
所有的上述这些情况,到了帕雷这边,经过他的实践努力和一些改良,把手术师这个职业的地位大大提升了,也推动了外科手术的进展。
终于轮到今天文章的主人公,安布列斯·帕雷登场了。
安布列斯·帕雷,他出生在一个16世纪法国的一个平民家庭。15岁时,他就跟着哥哥做理发匠,但是他对医疗,对外科手术,对于解剖学就特别有兴趣,学习特别的刻苦,然后他一路拜师学艺,最后到了巴黎医学院的一个实习机构-医院,也进行了几年专业的解剖学的学习。
后来一次战争爆发,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兰西开战了,他就应邀入伍随军出征。那个时候热兵器开始慢慢的运用到战场上了,很多炮火,火神枪的运用,跟那个时候冷兵器时期不一样。冷兵器时期可能是这个刀刃口挫伤这个皮肤,这个伤口不是很大,但是火药运用到战争以后伤口就特别的大,这个伤害的组织破坏力就很大,那个时候火药伤害了以后就会溃烂。大家觉得是不是火药里面有毒。所以那个时候处理伤口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那个烙铁烧红了去烫,你看一个伤兵已然够悲惨了,还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对待他,有多痛苦可想而知。另外,就是用滚油去浇在那个伤口上,来做杀菌或者说做一些处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细菌,但是他们会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安全。但是呢,第一会非常痛苦,第二这种处理方式伤口也比较容易化脓,愈合的也很慢。第三就算挺过去愈合了,最后也会留下一些疤。有一次,就是这个战役死伤很惨重,一下子有很多的这些伤员进来,那个时候连这个滚油都已经用完了,因为在此之前帕雷在民间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种方式处理好像有一些问题,他自己查了很多的古方,用玫瑰油,鸡蛋黄和松节油调了一种软膏,因为那个油用完了,他就用这种软膏来给这些士兵处理伤口,然后第2天醒来,他去查看这些人,那个涂了滚油的人就是一夜都没睡好,发烧的有些神志不清了,伤口愈合得也比较慢,但是涂了他的这个软膏的都美美的睡了一觉,伤口愈合得也比较好,从此以后他就把这个软膏的这种处理伤口的方式在军队里面进行推广。
另外就是止血,就算是处理好的伤口,可是失血过多,很多人会造成这个器官的衰竭乃至休克,也会造成死亡率的增高。帕雷发现,就是在离心脏较近的动脉把血管做很好的结扎就能够减缓血液的流失。所以,他也把这些技术和方法在这个治疗当中进行了推广,后来从战场上撤下来以后,他也研究了不同体位截肢应该在哪里做这个结扎效果更好,然后做了一些研究。
战争结束以后,帕雷也是功成名就,但是他没有沉溺于这种名望,或者说是奢靡的享受里,因为那个时候战场上下来很多人都缺胳膊断腿,或者说瞎了一个眼睛。他回到了家乡以后也在研究设计制造很多的假肢,人造的眼球等等来给这些士兵来用。
不仅如此,他还陆续发表了《创伤治疗》,《外科学》来介绍他在火炮伤,枪伤,截肢,骨折和妇产等领域的经验总结,这些均被认为是各领域的开山之作,并先后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在欧洲广为流传,由此奠定了现代外科学的基础,因为帕雷也被后人尊为“现代外科学之父”。
外科的技术,正是有很多像帕雷这样的医生经过了好多的实践探索,然后在千百万病人身上做实践,才有了后来麻醉,无菌,抗生素,等等技术的诞生。
读完帕雷的这段历史,我觉得我也有很深的感动和感受。帕雷作为一个平民阶层,敢于去质疑上千年的权威传统,常言道,文人相亲,在知识精英内部,学术机构内部,其实很多专家为了彼此的这种理念是可以吵成一团的,像我们现在大学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都有好多学派,彼此纷争相互争斗。但是作为一个草根,作为一个非知识精英阶层的人,敢于质疑,敢于去相信自己的思考实践,相信真相在病人的身体里,而不是藏在文本的教条中。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和胆略的,这一点非常让人佩服,就好比一个初中物理老师敢于去质疑相对论一样,它是一种革命的范式转移,这在我们今天当下的时代里,这种创新的精神也特别的难能可贵。
另外,我在读帕雷材料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则故事,我非常的震撼。就是有一次都灵战役非常惨烈,然后从前线抬下来一个伤员,整边的脸都被炮火给损伤的一塌糊涂了,他既看不见,也听不到,也不能说话,身边的人就问帕雷:你能想办法救他吗?帕雷就说我不能,然后他就在墙边自己一个人呆了一会儿,回过来,他就用了一把利剑割断了那个伤员的咽喉。然后身边的人就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残暴,你是撒旦附体吗?怎么可以这么做?帕雷说,刚才我向上帝祷告了,我想如果我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不能活了,而且也这么痛苦,我一定希望上帝能够派一个人,来结束我的生命,来对我进行拯救,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来干吧。所以菩萨心肠也有霹雳手段。
这就让我想到,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手段,像腹腔镜手术,微创手术,开颅开胸,达芬奇手臂,我们恨不得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设备,幻想把所有的身体的问题都交给医疗,可是在健康面前,任何的医疗手段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就像帕雷所说,我只负责治疗,神来负责治愈。当一切的医疗手段,技术手段都穷尽的时候,对生命,对人体的复杂,对生命的有限,我们永远要怀抱一份敬畏和谦卑。
本文为视频的文字版,视频请看历史记录上一条
转载请注明:http://www.cbusw.com/kxyy/122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