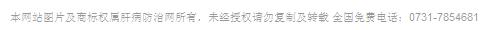阴差阳错,我们一大家子齐聚武汉,被封在家四十多天。焦虑许久终于趋于平静。虽恨病毒肆虐,哀民生多艰。但日子仍然要继续。万人的城市啊,在风雨中寂寞的摇晃。左边是封城,右边是生活。
武汉连续阴雨,连推窗望天都雾蒙蒙。周遭寂静,唯有阳台上的长寿花兀自绽放。花开引的小每每每天都要来惊叹:花苞全开了呀,我最喜欢大大的那一朵,花开完了呀……然后每每在花前叹气:唉,病毒啥时候走?我想到楼下的可多超市买巧克力,我还想上幼儿园……
足不出户的日子,让无忧无虑的四岁的小每每都惆怅起来。邻居在家用食材做了个小蛋糕,每每的妈妈花高于平常一倍的价格买来。每每不舍得吃,说:我想看五分钟。然后左看看右看看,又依依不舍的说:把公主留下吧。把小花留下吧。把星星也留下吧。唉,我还是最想爱莎公主蛋糕……我们都给她许诺,等战胜了病毒,一定把爱莎公主蛋糕送到她面前……在许诺中,蛋糕被我们瓜分完毕。
家里最气定神闲的是父亲。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看新闻。看武汉的新增与治愈数据,看天门是否零增长。然后督促我们每天打卡健康码。他郎的心早就飞回老家了。老家有亲朋打来电话,村里管控得力,一切安好。也有不好的消息传来:田叔突发疾病:中风,来不了,好在村里开了证明,医院,情况转好;村里的老支书我的大伯伯也在这场疫情里因为疾病离开了人世,一双儿女近在天门却不得相见,整个春节老两口孤单的在村里,把自己关在家里,直至大伯伯离世。
大伯伯是村里的老支书,也是我们的长辈。我婆婆在世的时候,认了大伯母为干女儿。那时候大父(我父亲的哥哥)参军,父亲年幼,作为军属,时任支部书记的大伯伯对婆婆诸多照顾,一来二去就认了干亲。其实我们叫大伯母为“恩妈”。那是小时候我们除了外婆家唯一可以随意走动的亲戚。大伯伯为人纯善,待父亲如亲兄弟一般,如今大伯伯离世,我们连凭吊的机会都没有,只有陪父母暗自神伤。
其实小人物的悲欢更能左右人的情绪。父亲这几天滴酒不沾,主动的下厨房为我们准备食物,还主动的给几位亲人打电话问候。非常时期更能显得亲情的可贵。虽然我们被困在武汉,身处险境,但全家人在一起共进退,相互鼓励,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母亲是家里最躁动不安最难安抚的。封城之初,因为我们在超市没有买到花生米,没有囤到足够多的大白菜,硬是要下楼到菜市场亲自去买。还一脸不屑的说,我就不信下个楼能si人。妹妹苦口婆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威逼利诱下终于成功的阻止了母亲。
看到电视里日益增长的数字,母亲终于感到了害怕:小时候听老人讲,有个村里si了四十多个人,没想到现在更多。
我们安宁的生活差点在某一天早晨被母亲打破。母亲清早起来,说肚子疼的要命。疼的死去活来的那种。医院都去不了。我硬着心肠说,忍。再疼也要忍。母亲自己把自己吓着了:我父就是阑尾炎疼的穿孔被抢救过来的,我这是阑尾炎……我不能在你妹家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下楼……
我赶紧让妹夫咨询他当医生的姐夫,是否真是阑尾炎发作。得知不是阑尾炎,悬着的心放了一半,安抚母亲情绪稳定,拿了一颗去痛片暂时止疼,让母亲卧床休息,然后下楼与妹妹商讨办法。平常百姓人家,连小区门都出不去,实在病不得啊。幸亏母亲只是肚子疼,缓过来就好了。
因为这场突来的疼痛,母亲成了我家的甩手掌柜。我彻底的接管了厨房诸多事务。
小时候我们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依靠父母的关爱度过了单纯美好的童年少年,直到离开家离开父母的怀抱成为他乡人,除了逢年过节,很少再有机会与父母长时间相处。这段被封的日子里一大家子围在父母身边,朝夕相处,我们有幸为父母温粥煲汤,侍奉左右,深刻理解了父母的艰辛。
单是每顿十几人的生活,足够操心了。幸亏我有当厨师的潜质,也有一颗爱家人的心。每天不厌其烦的在厨房推陈出新。
从没做过面食的我,竟然百度做了一锅水煎包子。从发面到剁馅到包包子,然后下锅煎熟,一气呵成。哪里像个新手,完全做出了面点师傅的气场。
与母亲谈起包子馒头往事,母亲深有感慨。那时候外婆家家境殷实,每次蒸馒头都用大蒸笼蒸好几格,然后给我们送来。一般人家根本蒸不起馒头。而我最惦记的是学校门口的煮包子。在清寒的学生时代,那是世间最美的食粮。我曾经想,能开那么一间煮包子店,也是极好的。
看我无师自通,竟然年轻时还有开煮包子店的愿望,妹妹慷慨许诺,等有钱了,我们去岛上开个煮包子店……在大家心照不宣的哄笑声中,一锅煮包子又被抢光。。。
我们的日子就这样缓缓滑过。。。很快,就能看见曙光了。
?文字:流苏
扫码
转载请注明:http://www.cbusw.com/zzjc/12896.html